
Official Notices
官方资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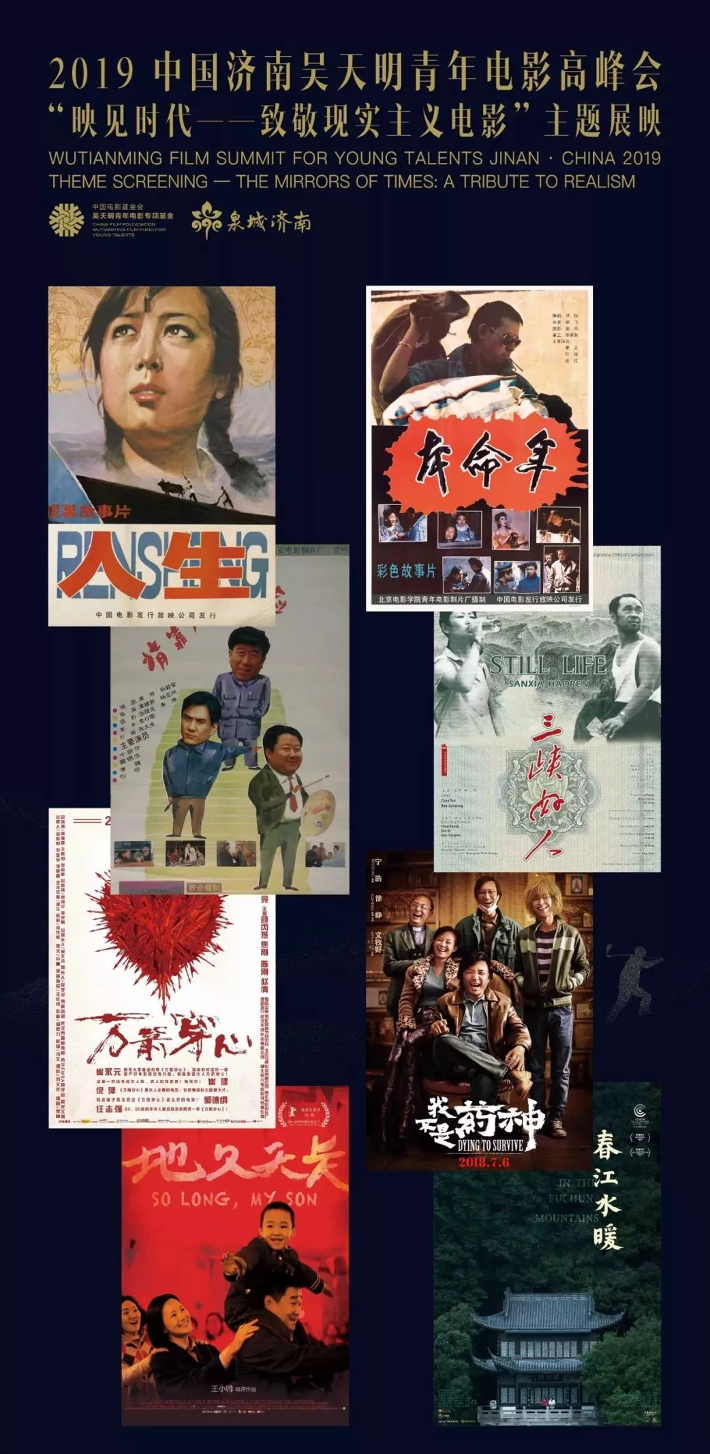
映后交流
王飞飞:很高兴今天能够继续参加“映见时代——致敬现实主义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很荣幸邀请到王竞导演,我是在2012年看的这部影片,昨天又重温了一遍,感觉真的太好了。对我来说,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看这部影片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影片中好多个共鸣点的感受是有所区别的。比如,在二十多岁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当时不太理解,李宝莉她丈夫去世后,为什么当时她丈夫没有给她留话。但是我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丈夫对妻子最大的报复或说最大的伤害就是没给她留话。对我来说,那种感受是挺强烈的。因此,今天想问问王导演,您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拍摄这样一部影片?
王竞:首先,我先与济南的观众打个招呼,大家好。非常荣幸能跟大家在这里做交流。其实我不太记得你刚刚提到的情节是编剧写出来的还是原小说里的,但是这一细节很重要,它代表了李宝莉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定位以及在家庭中起的作用的一种看法。其实她对丈夫没有给自己留话是非常不满的。在她看来,她付出了这么多,最后却在丈夫心目中没有一点位置。设身处地地想,生活中的母亲或者父亲,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想法。这涉及到对这一人物的评价问题,在我们看起来,李宝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或是完美的妻子,她身上有她自己的问题,而我们更希望这一角色是一个能让人思考的角色。

王飞飞导演、王竞导演
王飞飞:对,我觉得这一形象与观众们之前看到的女性形象差别还是很大的。她身上有比较明显的性格缺陷或说短板,包括对丈夫、对孩子的控制等。在关键节点上,导致了整个家庭的悲剧。这部电影是根据方方老师的小说改编的,您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决定把这部小说变成电影,当时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王竞:其实这部电影与吴天明导演还真的有关系。当年是吴天明导演找我拍一部儿童电影叫《孩子那些事》,这个电影拍完之后参加了无锡国际电影节,得了评委会奖。这届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是谢飞老师,他看到了影片之后,就问我在忙什么,我说我没忙什么。谢飞老师就给我推荐了方方老师的这部小说,随后寄给了我。
王飞飞:所以是谢飞老师把小说推荐给你了。
王竞:对,因为谢飞导演他自己可能对此类女性题材比较敏感,很关注。我看完之后,花了一点时间整理思绪,我在考虑我到底能不能拍它。因为小说中李宝莉的形象一下就会抓住你的注意力。她身上有特别强的生命力和生命感,因而她是一个能够让人感受到力量的角色。但是原小说与电影不一样的地方是李宝莉后半生的故事。这一部分其实改动挺大的,跟原小说很不一样。在原小说中,建建这一角色比现在的社会地位要高,开着酒吧,比较有钱。后来,我们去找方方老师,问她怎么看李宝莉这一角色,方方老师本人特别喜欢这一角色。在她心中,李宝莉是中国女性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其实,有缺陷的角色都是非常成功的角色。我们编剧其实也是个女性作者吴楠,她参与过好多影片,比如《七月与安生》。当时找到她的原因,一是因为她本人是武汉人,这部小说中有浓郁的武汉气息。二是因为她是女性,她对角色的把握会更准确,会还原真实的角色。在结局部分,没有让李宝莉有个完美的结局,也没有让她得到很多温暖,其实是让编剧往下压制了一下。

王竞导演
王飞飞: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人生,包括您刚提到的对于建建这一角色的修改,如果建建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角色,我觉得对影片整体的气氛是一种破坏。
王竞:我希望观众在看完影片之后,对角色能有思考。
王飞飞:或者说观众看完影片之后,感觉这就是身边的邻居,或者是曾经认识的邻居。
王竞:对,这样的感受和反馈也能促使自己做出思考和反省。
王飞飞:其实这部影片在2012年的时候,拿到了国内许多奖项,包括第15届华表奖最佳故事片,而李宝莉的扮演者颜丙燕老师,几乎拿遍了当时国内的最佳女演员奖项。我觉得王导您特别善于挖掘演员身上不同的特质,像您的处女作《方便面时代》的李亚鹏、《我是植物人》的李乃文,他们都是通过影片得到广泛认可的。而在这部影片中,除了颜丙燕老师外,您还挖掘了一个现在当红的男演员李现。所以就想问问,对于演员的挖掘和合作方面的心得和见解。
王竞:其实拍电影主要是讲人的故事,而一个角色在影片中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当年李亚鹏那一角色也好,还是这部影片中像颜丙燕、李现这样的角色也好,需要成就的是角色本身。像《万箭穿心》这部电影是一个讲人的故事片,那么在看完影片后,观众脑子里留下的应该是人物形象,而不是画面或者其他东西。所以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能超越人的定位,最后呈现的就是人物。演员的表演其实是为了塑造角色,最后成就一个角色。其实应该让演员自己发挥出他更多的可能性。

王竞导演
王飞飞:其实您自己是摄影师出身,也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系主任。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实际上应该是比导演系更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地位,中国电影几乎所有一线的摄影师基本全是摄影系毕业的。您自己是摄影师出身,但是这部影片在影像处理上其实蛮质朴的。很多国内导演大都是从摄影师转到导演,这也算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优良传统,从张艺谋导演开始。到顾长卫导演,然后到您,所以想问问,从摄影师转导演的优势是什么?
王竞:其实我们私下也聊这个话题,在别的国家,导演很多时候是从演员或者编剧转过来的,但是中国却是摄影师转导演。我也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我们觉得可能一个客观的原因是摄影师本身有技术门槛。
所以摄影师将来不太容易被替代,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生存率相对高。最近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学生毕业4年卖电子烟过活,很有感触。但是摄影系毕业之后,如果想不卖电子烟,他肯定能不卖电子烟。一位新导演刚刚出来的时候给你几百万、几千万,让你去拍你自己的作品可能比较难,所以到最后他的存活率就低。
这不是说摄影系的学生比导演系的学生更优秀,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技术让他在行业里面生存的时间会更久,而原先导演系毕业的很多导演已经改行了。这不是开玩笑,但当我们分析,这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好事,比如张艺谋他们班,几乎一个不落全部转行做导演了。其实这也说明大家在影像上的执着和坚持还不够,或者说导演这个职业的诱惑性更强一点。
王飞飞:那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曾看到一个说法,其实除了导演和主演之外,对幕后的工作人员,像摄影师和美术可能尊重和关注不够多。您觉得是不是与此有关?一部影片,大家可能都在关注导演和主演,对于优秀的摄影师和美术师等其他工种,相对而言有失公允。
王竞: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不能把原因都归在这上面。其实还是导演的个人表达空间更大,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更过瘾。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作为一个摄影师或美术师,可能还没有找到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工作魅力和价值。您刚才提到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是电影行业里做的最好的。
王飞飞:对,应该是金字塔尖上。
王竞:从行业来看,进入到行业主流里面的,真正算起来的话普遍都是摄影师。但是客观地反省的话,相比国外的同行来说,其实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我今天可能推荐去看好莱坞大片,看后你似乎觉得画面还行,但是还真没有在国际上获得一流奖项的摄影师,也没有对影像美学做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师。所以,我们离最顶峰的创作高度还有距离。

映后QA
王飞飞:那看过影片后,现场观众对这部作品有什么问题可以跟导演交流交流。让我们把话筒交给观众。
观众:王导演您好,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电影。我七年前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感觉非常惊艳,感慨万千。七年后,我依然觉得这部影片是一部现实主义精品力作,它一点不逊色于现在任何一部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下王导,整部影片的影像风格明显偏纪实,用了大量的手提摄影或者是摇镜头,包括武汉方言的使用。但是,在整部影片的风格之余,我又听到很多地方使用到一种音乐,当然音乐和纪实有时候并不煽情。请问王导,为了更大程度还原纪实的风格,您在音乐的运用上,是如何考虑的?
王竞:谢谢您的问题,我觉得您问的很专业。当初我们在确定影片风格的时候,就确定它是一个比较朴实、接地气的影片,影片讲故事的口吻也应该是比较口语化的。此外,即便摄影机带有三脚架,但其实它是垫了东西的,隔着手,让它能有一种呼吸感。对于音乐的使用比较节制,没有使用太多煽情性的音乐。归根结底,我们希望这部影片的生活感会更强,让大家能够觉得没有距离感。

观众:谢谢王导,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在这部电影中,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其实是特别有代入感的。因为这种女性在我们生活中特别常见,她们性格泼辣直爽、敢爱敢恨,但是又忍辱负重,甚至可能会为了家庭失去自我。但这样一种失去换来的是家人或者社会的不理解。本来这个女人不信命,她不信这个邪,但是最后她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或者挫折之后,她说就这个命,她就相信命了。所以请问您对这一女性这样一种前后对命运的认知是怎么理解的?请问您个人相信这种宿命吗?
王竞:其实我们总结这部电影主题的时候,我们就在考虑如何去定位它的主题,后来我们把它总结成:一个强势的女人输给了比她更强势的命运。说起这个命,我认为李宝莉本身她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她一开始一直不认命不信命,到最后她对自己的命运妥协了。我们在总结李宝莉这个悲剧人物时,其实已经把这个人物想透了,不想透是没有办法开始去创作的。仔细想想,如果李宝莉的人生是一个悲剧的话,她的悲剧点在哪儿?到底什么是她的悲剧?是性格强悍还是其他原因,比如她不知感恩的孩子和懦弱的丈夫。
但是这都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没有对李宝莉本身进行解剖,她的命运悲剧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找到。偶然有一天,我当时看一个杂志上谈卡扎非的一个报道。这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觉得一下找到了根源。报道指出卡扎非的悲剧在于,他用古代酋长的理念去管理一个现代国家。我突然觉得她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用一个特别简单的思维去对抗一个家庭的复杂问题。
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的相处,其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怎么跟父母相处?怎么跟妻子或者丈夫相处?怎么去面对一直在长大在变化的孩子?这个过程既需要耐心,也需要知识,还需要智慧,非常有难度。但是学校并不会教这个东西,它也不是一门课。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在用一个新生的姿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面去磕绊,结果又是一个摆脱不掉的那么密切的一个新环境,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好这一路。李宝莉就是走得不太好的不幸的一个人。此外,李宝莉她本身是一个简单直接的人,她的性格特别像武汉人的性格。武汉是一个码头城市,本身人来人往,你要弱的话你在城市里就会吃亏。
王飞飞:就生存不下去。
王竞:对的,就难以生存下去。城市要求你快速应对各种各样东西。类似于,你要欺负我马上就打回去。这样说不算是诋毁武汉人,因为我们去武汉的感觉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李宝莉身上有非常典型的码头城市人民的这种影子。
王飞飞:重庆的影子。
王竞:对,重庆可能也有这样的。
王飞飞:还有南京。

王飞飞导演、王竞导演
王竞:可能也是。她比较强势,她比较直接简单。但是她丈夫就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人,她丈夫是工厂里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其实是一个有点文化,又比较敏感细腻的人。其实她的婆婆也不简单,婆婆是小学教师。儿子更不简单,儿子是高考状元。实际上,她面对这样一家人的时候,她简单直接的性格会给她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她就一直往前走。所以这个家里的磕磕绊绊,是一个非常复杂问题。
王飞飞:所以最后就反噬了。比如说在天台上,我当年看的时候,体会不太到那种感觉。但是我昨天重看的时候,感觉到她巨大的压抑和痛苦。
王竞:尤其是对一位奉献半生的妈妈来说,那是非常残忍的报复。
王飞飞:对,非常残忍。我觉得女性导演不一定敢这么处理,可能只有男性导演才有这方面考量。我看完之后,稍微缓了一会儿。我七年前看的时候,以为这就是正常的母子之间的争吵,但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再看,我觉得直接判了死刑,对于人物来说实际上是非常残忍的。此外,焦刚老师把这个丈夫演的非常的好。还有其他观众要提问吗?

观众:我觉得在您的电影里,现实主义的核心可能就是矛盾的产生和它的消解。电影里面体现的就是母亲、父亲、奶奶、孩子之间发生的矛盾,把矛盾消解了就成为了生活,消解不了可能就成为了悲剧。我是一个普通影迷,之前也看过您其他的作品,我觉得现实主义核心也贯穿在您别的作品中。比如《无形杀》涉及网络搜索,搜索和被搜索人的矛盾的消解;《我是植物人》是医患之间的矛盾的产生和消解。我个人最喜爱的电影是《大明劫》。我觉得《大明劫》里含有一种广义的现实主义,可以分为一种历史现实主义,还原历史空间里体现的现实主义。相对于其他的历史题材影片,《大明劫》的切入点从冯远征演的医生和戴立忍演的将军入手,将他们放置于明末清初这样一个历史场景里,别的导演很难找到这样的切入点。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您从现实出发,透视出历史现实主义的一种体现呢?
王竞:对我来说,现实主义是我唯一会的或者唯一能用的方法。哪怕后来拍奇幻片,它也是广义上的现实主义。虽然说描绘的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它是一种表现现实主义。
王飞飞:精神内核是。

王竞:对我来说,现实主义是唯一值得探索的一个手段。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思考的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其实我们做导演,是想对这个世界发表一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所以现实主义差不多算是唯一的出口。就广义的现实主义来说,它不一定非得都是现实题材,哪怕你拍一个科幻题材和历史题材,也是现实主义的,就像克罗齐说,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我们都不是过去的人,但是对那段历史发表一下见解,是对历史的一种回应,只不过使用了现实的逻辑。
王飞飞:昨天有观众说,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的护身符。
王竞:对,对我来说是护身符。
